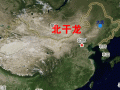古人的数字,不仅用来计数,也用来表达哲学观念
- 命理
- 2022-11-02
- 9
世间万物都有机缘。两道平行的脚印,也可以奇妙地交际在一起。
大概三百多年前,德国人莱布尼茨可能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他一生都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和热情。
因为这层关系,还引发了一桩著名的公案:莱布尼茨创造的、应用于计算机系统的“二进制”算法,是否受到了中国太极八卦的启示?
其实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附会,然而莱布尼茨在发明了二进制之后,也确实表示过,他在“伏羲先天卦序图”上找到了相通之处:
“这张图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可能已有几千年时间不为人们所理解。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这的确令人吃惊。”
如果以易卦的阴爻代表0,阳爻代表1,那么一卦之象,就是一个二进制的六级表示式。
一张卦序图,从卦气说,包含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辩证法;若以二进制解读,则变成了完全形式化的数学的含义。莱布尼茨殚精竭虑想出的二进制,似乎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以自己的方式从宇宙中悟到。
我们一般觉得,中国人是善于感性的。然而,面对这个世界,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也有“大道至简”的数学模式。“凡不可见之理,寓可见之象者,皆数也。”数,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也蕴含了丰富的生命特性。
古人的数字,不仅用来计数,也用来表达哲学观念。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每个数字,都有其象征意义:一元,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极,九宫……九为数之究,十为数之具……
凡此种种,对于我们来说,既玄而又玄,也耳熟能详。
中国的哲人,非常关心宇宙生成问题。对宇宙进行具体推演时,非有数字不可。
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个数,地数五个数。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也是通过天数与地数,一生一成,相合而来。
在哲学家解释自然的过程中,神秘的数字,建立了一种隐喻或象征的关系。以至于《说文解字》作为一本字典,对于从“一”到“十”的基本数字的解释,也均带有浓郁的宇宙论色彩。
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中国先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
数,有生成万物之性。朱熹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关系,每一事物都有一太极,包含着生生不穷之理。他拿一棵树木比作太极:先分出枝干,再分为花和叶,等到生出果子,果子里面,又会“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
在《周易》中,“数”与时间、空间、自然以及人的命运都有关,它们互相结合、联系和变通。太一不仅可以生出阴阳两仪、春夏秋冬四时,还可以产生八卦之象。以八卦为原型的河图和洛书,均以数的排列,来象征宇宙的时间和空间。
数字,令许多人为之着迷。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中国哲学与其有颇多相通之处,然而也有很大不同。
在古希腊人那里,“数”是世界的本质,并把它绝对化和神秘化。但是中国人认为,“数”只是天地之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工具。如杨万里说:“天地之道不在数也,依于数而已。”而且,“数”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在生成与变化中。
古希腊人从数学出发,用明晰的比例,来解释宇宙的构成和美。中国人从生命出发,用“数”来表示生命的生成过程,是生生而条理之秩序。
古希腊的“数”,开启的是空间性美学,通向的是固定不变的形体。中国的“数”,开启的是时间性美学,“数”通向的是一个无限开放、绵延广阔的世界。
《周易》通过“数”,所阐发的生成之道、生生之德,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表现特色。
当“数”不被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学符号,而是一种富有生机、可虚可实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有了传神达意的审美功能。看似严肃枯燥的数字,在灵心妙笔的点化下,也可构成不凡的意蕴,扩大艺术的意象。
宋代哲学家邵雍写过一首著名的“数字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一首五绝,寥寥二十个字中,有十个是数字。然而,数字堆叠在一起,不仅不显得乏味,却是如此轻松活泼,像一幅错落有致的风景画,生动而写意。
邵雍能够创作出这首诗,似乎并非偶然。作为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邵雍也是一位易学大师,莱布尼茨看到的“伏羲先天卦序图”,就是邵雍托名伏羲所作。
看看邵雍如何让数字绘成画:一去,诗有了动感,万物皆入我心;二三里,诗有了空间距离;四五家,悠然地分布、散落开来;六七座、八九十枝,世界不知不觉地打开,融融春意已扑面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序列排开,仿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关系,又暗涵着“一元复始”的春回大地。
十个数字,虚实相间,简约而丰满。想必邵雍对数字有独特的感悟,才能自如地掌握数字的密码。
当然不只有哲学家会用数字写诗。许多文人也懂得让数字入诗入词,跨越抽象与形象、情感的鸿沟,令数字产生诗意。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苏轼《水龙吟》),不可捉摸的情感,用简单的数值划分,极富情趣地传达出来。
“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辛弃疾《西江月》),妙用数字,写景抒情,烘托清幽的夜色,增添了灵动的趣味。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进芦花皆不见。”(无名氏《雪景》)一连串数字排列,很像邵雍的那首诗,却多了些质朴。随着数字构成的旋律,飘雪越来越密、积雪越来越厚的动态图景,已经呈现在眼前了。
当雪花与芦花融为一体,读者也随之进入了空阔浩茫的境界。立象尽意,中国艺术的精神正在如此。
中国人连一个数字都不肯让它变得冰冷。正如在中国人的哲学观念里,宇宙不是一个物质的场所,而是一个生机盎然、有条理、有情感的宇宙。
在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之后,狄德罗曾如此说道:“伏羲使用的两种线符,其实就是二进制的基本要素。一个智力非凡的民族已经做到了用整世纪整世纪的时间,对只能到莱布尼茨才能发现的奥秘进行了毫无结果但又毫不气馁的探索。”
狄德罗的话中,不乏对中国的恭维和同情,然而仍充满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却不知中国的“数“本来就有本质区别。或许,两道平行的脚印可以在宇宙的某处交际在一起,然而并不意味着那是双方共同探索的目标。
中国人观察万物采用两个最基本的维度:象与数。“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千变万化的世界,“数”则是这个世界中呈现的秩序。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形上学和宇宙观是非数学、几何学的,因此与近代科学完全不同。譬如,西方从古希腊泰勒斯开始,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本,是不变的实体;而中国哲人,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等,以水喻道,但不以水为哲学实体。
同样,中国的“数”,与西方科学的、数学的“数”,有根本不同。因为中国之“数”是“生成的、变化的、象征意味的”,也是“流动性的、意义性、价值性的”。
“中国之数为节奏与和谐之符号,故有中心之黄钟之声、之数,以生其它音与数。是一完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之数,遂成为生命变化妙理之‘象’矣。”
有意思的是,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后,似乎也不知道可以用它来做什么。直到两百多年过后,二进制才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
在中国,先贤的哲思也曾是指向未来的:诸多艺术中,阴阳共生、立象尽意、形似不如神似的理念,以及绘画的墨有五色、音乐有五音十二律,等等……都能体现出“数”的影子。
最好的作品,就是带来启迪最多的作品。“数”的生生不已的精神,在不断的拓展和弘扬中,成为了我们自觉的文化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与其在故纸堆里故弄玄虚,不如从中重新建构我们的价值取向、美学原则,以及更多的东西。